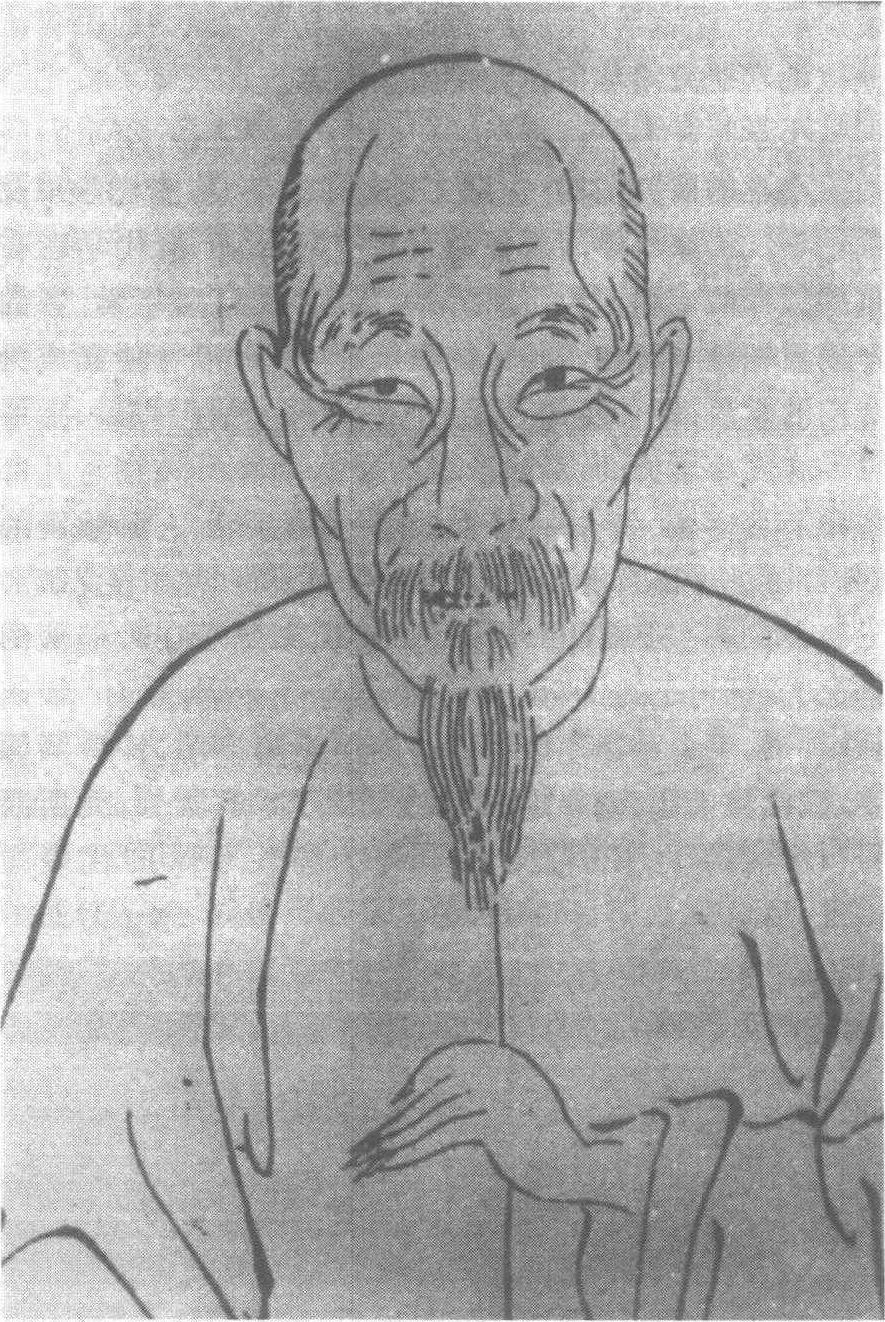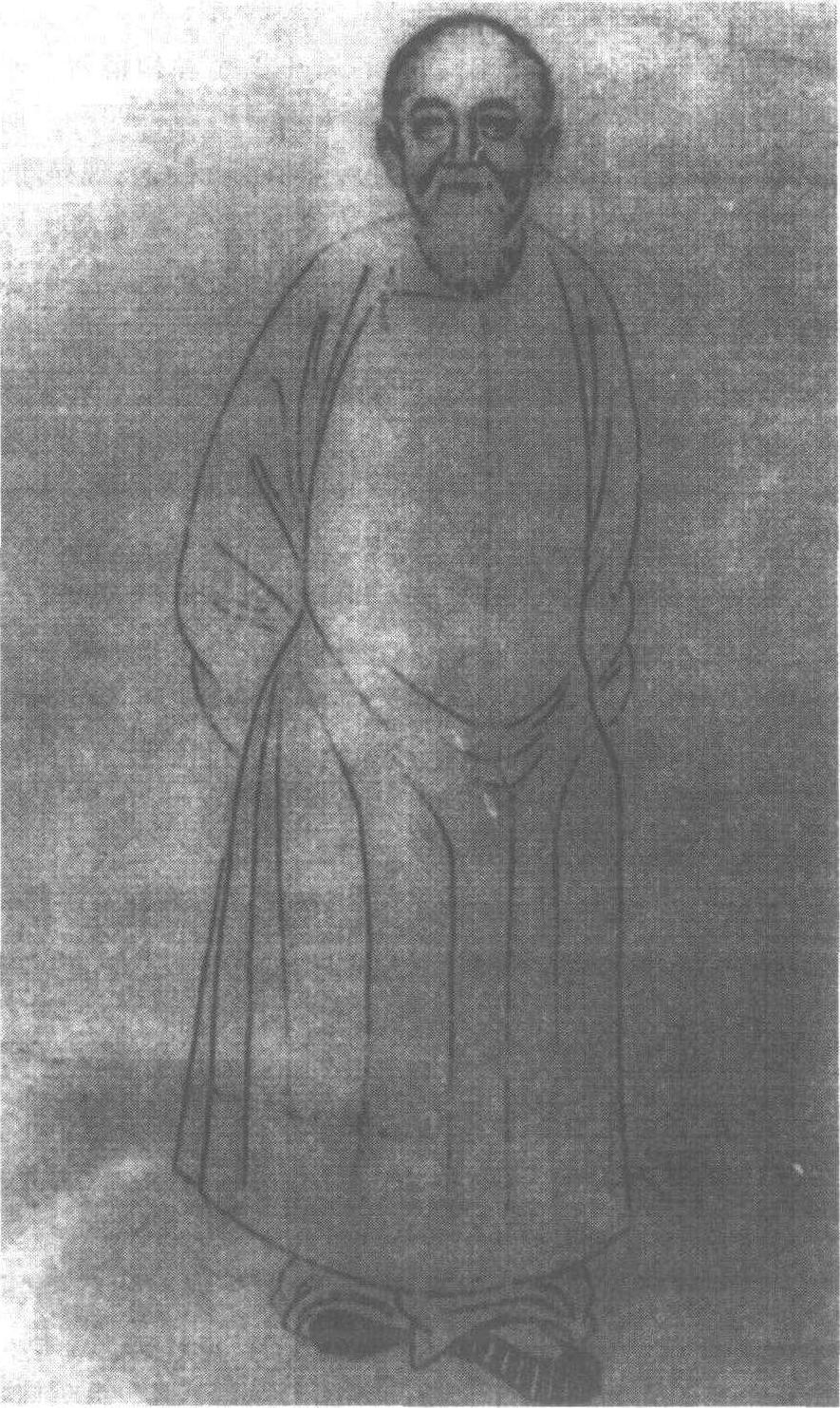幽微章句—清代儒学·文化高峰·异彩纷呈:专科学术的发展与兴盛
以汉学复兴为特征的清代学术,其文化价值既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清理和总结,同时也反映在各门专科学术的发展。正是对古代典籍的大规模整理工作,推动了经学、小学、史学、地理、天算、校勘、辨伪、辑佚、目录、版本等各个具体学科的发展,使一代学术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画面。
经学
经学,即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历代封建文化的主体,清代也不例外。可以说,清代学术界对宋明理学的反动,以及对汉学的回归,最早就是从经学开始的。影响所及,清代经学研究进入全盛阶段,各种经学著述汗牛充栋,“有证注疏之疏失者,有发注疏所未发者,亦有与古今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之折衷者”(夏修恕《皇清经解序》)。综观清代经学研究的成绩,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宋代理学兴起之后,学者为了建构其理论体系,往往强解经书以就己说,甚至不惜造伪以为立论根据,造成诸多误释曲解,严重淆乱了经书的本来面貌。清代学者一洗前代空疏之弊,以比较客观、求实的态度,致力于各部经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廓清了后世学者人为笼罩在经典研究上的迷雾。如胡渭的《易图明辨》、阮元的《论语论仁论》等篇,或力图还经籍以本来面目,或努力寻求经义原解,基本上达到了汉学求真求实的境地。
其二,搜辑钩稽汉人经说。清代学术界以复兴汉学为鹄的,汉代的经师经说,受到学者的特别重视。许多学者穷毕生精力,爬梳钩沉,使得许多亡佚已久的汉代经说得以重见于世,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便利。如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九经古义》,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都是搜辑钩稽汉代以及古代经说的代表作。
其三,撰著新注新疏。在清代汉学复兴过程中,学风日益由空返实,实事求是成为学者一致遵循的准则。本着这种客观求实的态度,学者在抛弃空疏的理学的同时,也开始觉察到汉学本身也并非完全正确,汉代的经师经说同样也存在着诸多误解谬说以及相互牴牾之处。因此,一些学者试图超越汉宋,综括前代,为儒家经典撰著新解。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胡培翚的《仪礼正义》,陈立的《春秋公羊传义疏》,焦循的《孟子正义》,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等等,几乎各部经书,都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集成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经学研究的新成果。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学者还十分注意汇辑刊刻本朝经学研究著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皇清经解》和《续皇清经解》两部大书。前者系阮元主持汇刻,他发凡起例,组织贤俊,从本朝学者解经专书以及各家文集、杂著中,选择有价值的著作篇章,按作者年代先后顺序排列,汇刊成《皇清经解》一书,共收七十三家,一百八十三种著作,计一千四百卷,清代前期经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基本囊括其中。《续皇清经解》则系清末王先谦所刻,他仿照《皇清经解》的体例,汇辑诸家著述,刻成《续皇清经解》一书,计一千四百三十卷。二书遂成为总括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精华的重要汇编本。
小学
小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囊括了文字学、音韵学以及训诂学。历来小学附属于经学之下,但由于清代学者在这些方面的专精研究,使得附庸蔚为大国,文字学、音韵学以及训诂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相对独立成为专门的学科,即传统语言学。
在文字学方面,清代学者的成就集中反映在对几部古代著名字书、辞书的整理、注释和疏解上。如戴震的《方言疏证》,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等等。特别是《广雅疏证》一书,王念孙运用因音求义的理论与方法,探寻同源字,破读假借字,阐释连语,所释无不“冰解壤分,无所凝滞”(章炳麟《九书·订文》),被誉为清代小学的代表之作。

段玉裁(1735—1815),江苏金壇人。清代经学、训诂音韵学家。著有《说文解字注》等。
在音韵学方面,清代学者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古韵分部体系。古音学的研究,源于宋代的吴棫、郑庠。由于历史的变迁和地域的差别,古今语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六朝隋唐的人读先秦诗歌或韵文,已多有不谐之处。但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由于古今语音不同的关系,为了求得音韵的谐合,他们或改读字音,或改换文字,影响了古代典籍的本来面貌。到了宋代,这种风气更为盛行,所谓“叶音”说成为通例,甚而出现一字数叶、一音数读的现象,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看到了“叶音”说的矛盾,开始把当时韵书上的韵部通合并用,以求古书读音的谐合。这就是吴棫提出的通转说,依照他的说法,当时韵书所分一百零六韵可以归并为古韵九部。其后,郑庠又并为六部。这可以看作是古音学研究的滥觞。但由于他们缺乏历史观点,仅从当时韵书上韵部的通转着眼,因此,虽然对古韵作大致的分部,但各部之间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转,并没有解决古音问题。直到明代,陈第才明确提出用发展和变迁的观点来研究语音,把古音置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和地域环境内进行分析,使古音学的研究开始走上了较为正确的道路。清初,顾炎武将陈第之说又推进一步,全跳出韵书的窠臼,直接根据《诗经》的押韵情况,分古韵为十部,从而奠定了上古韵部体系的基础。其后,江永、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诸家继有研究,分部日趋细密。从十三部到十七部,再到二十一部,最后定为二十二部,被后世学者誉为“古韵二十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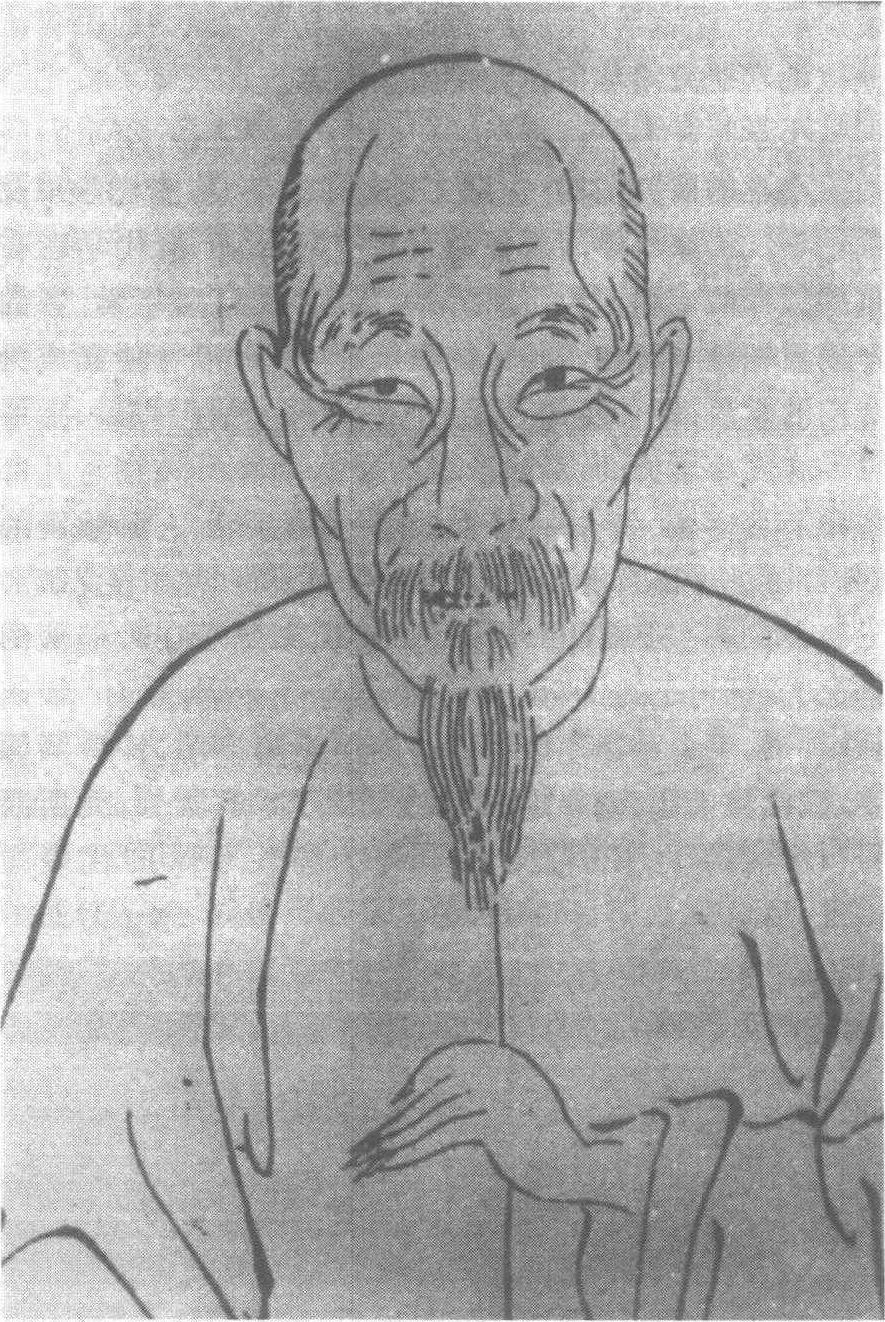
钱大昕(1728—1804),嘉定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精于音韵、训诂、历算、金石等。著有《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等。
古韵分部而外,清代学者还注意到了上古音的声类问题。钱大昕根据自己的湛深研究,提出了“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独到见解,至今仍被音韵学家视为定论。陈澧所著《切韵考》一书,则依据《广韵》中所录陆法言《切韵》之反切语,把声纽(即声母)分为四十类,其中清声为二十一类,浊声为十九类。陈氏的研究,既反映了清代学者在古音声类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时也为后人开启了途径。
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既对群经诸子及相关典籍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训释,又对古代典籍的文字训诂作了一番整理汇总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阮元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一书。该书计一百零六卷,“以字为经,以韵为纬,取汉至唐说经之书八十六种,条分而缕析之”(阮元《定香亭笔谈》卷四),凡经书史籍本文诂训,传注文字读音、释义及假借等等,均网罗殆尽,并据《佩文韵府》按韵编排,各韵自为一卷。每字之下,先“以本义前列,其引伸之义,辗转相训者次之,名物、象数又次之”。引用诸经,则仿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先《易》、《书》、《诗》,次《周礼》、《仪礼》、《礼记》,次《左氏》、《公羊》、《穀梁》,次《孝经》、《论语》等”(《经籍纂诂· 凡例》),并旁及《史记》、《汉书》、《战国策》、《荀子》、《墨子》、《楚辞》、《文选》等诸多古代典籍。所谓“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王引之《经籍纂诂序》),堪称“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臧庸《经籍纂诂后序》),实际上成为古代典籍文字训诂的总汇,也是后人检寻旧诂的重要工具书。
史学清代学者的史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对前史所缺各种表、志的补作,以及对旧史的清理考证两个方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自司马迁、班固创立纪传体通史及断代史专著的体裁之后,史表、史志便成为史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有谓“读史以表、志为最要,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之语。但由于种种原因,历代正史的表、志多有阙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清代学者十分重视史表、史志的作用,花费很大的功夫对历代正史的表、志作了一番全面的拾遗补阙的工作。诸如钱大昕的《补续汉书艺文志》,洪亮吉的《补三国疆域志》,徐文范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钱仪吉的《补晋兵志》,郝懿行的《补宋书刑法志》、《补宋书食货志》,倪灿的《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补志、补表不下数十种,古史所阙略者,几乎囊括无遗,梁启超盛称“凡此皆清儒绝诣,而成绩永不可没者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洪亮吉(1746—1809),江苏武进人。清经学家、文学家,有《春秋左传诂》等行世。
拾遗补阙而外,清代学者还对历代史籍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清理考证。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当推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大家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和《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囊括了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的十九种史书,王鸣盛把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分别“统言之”,视为唐和五代二史,故称“十七史”。该书按诸史先后顺序排列,分条考述,对每部史书的文字、史实、典制、舆地等进行了细致的校勘和考证,对历代重要史事、人物以及史书也发表了自己的议论和看法。《廿二史考异》则是钱大昕考订校勘历代正史的集成之作。书名“廿二史”,实际上包括二十三种史籍,即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而加上《续汉书》一种,因《续汉书》不在正史之列,所以书名仍称“廿二史”。在这部书里,钱大昕运用其经学、小学、天文、地理、典制、金石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对历代正史进行了精细的考订和校勘。与王鸣盛、钱大昕的著述相比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则别具特色。该书所记起自《史记》,迄于《明史》,共计二十四种史书。赵翼沿袭明人“二十一史”的习惯说法,把《旧唐书》和《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分别合为一部,再加上清初纂修的《明史》,故称“廿二史”。在这部书中,赵翼以随笔札记的形式,对历代重要史事、典制、人物以及史书等作了综合的考证、分析与评论,而尤以对各朝各代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钩稽、归纳为多,使得该书别具思想深刻、见识卓越、方法精审、内容通俗的特色,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校勘清代考据学发达,对古书的校勘受到学者的特别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因此,清代学者普遍从事历代典籍的校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首先表现在校勘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精密。一般说来,校勘的方法不外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所谓对校,就是用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相互比勘,发现异同,择善而从。再说本校,即依据所校书本身的行文之例以及遣词造句的风格,比较其前后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这是因为古人属辞作文,往往有一定的语言习惯,每一时代的文字风格,每一作者的遣词特点,都是有迹可寻的。所以,根据所校书本身的文例以及它的语言习惯,来订正该书的讹误,也能收到显著的效果。至于他校,则是以他书校本书。凡所校书籍,其材料有采自前人书中之处,校勘时便可用前人的书来校;有被后人的书引用之处,则可用后人的书来校; 同一材料有为同时代的书所并裁的,还可用同时代的书来互相校勘。而理校,则是据理推测所校书之正误。这是诸种校勘方法中难度最大的,它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要有精审的裁断。清代学者熟谙对校、本校、他校之法,而尤善理校。他们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渊博知识,旁征博引,贯通裁断,不仅解决了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而且把校勘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清代校勘学的成就还突出地反映在对历代典籍的全面清理和校勘。官修《四库全书》,对著录、存目的上万种古代典籍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或鉴别版本,或辨正讹误,或考证异文,在很大程度上梳理了传世书籍的面貌。而众多学者穷毕生精力,对古代书籍进行的精审校勘,更集中反映了清代校勘学的水平。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校先秦两汉古书,所著《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和《经义述闻》,订讹补缺,归纳条例,成为乾嘉时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钱大昕、王鸣盛专校历代史籍,所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考辨异同,刊正讹误,被推为诸史研究的巨擘。段玉裁一生精力荟萃于《说文解字注》中,校勘注释,发明颇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古书原貌。阮元则组织一批学者遍校十三经,主持刊印成《十三经注疏》并《校勘记》,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
辑佚清代辑佚的成就,首推《四库全书》内收录的《永乐大典》辑本。《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类书,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保存有不少元代以前的珍本秘籍,号称“遗编渊海”。清代初年,随着学风的变化,以及辑佚风气的兴起,《大典》的文献价值逐渐被学者所认识。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借皇帝下诏访求书籍之机,提出搜访校录书籍的四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辑校《大典》。于是,由《大典》的辑佚工作直接导致了《四库全书》的开馆,而辑佚工作本身也随之成为《四库全书》编纂的一项重要内容。乾隆皇帝亲自规定采辑标准:“其书足资启牖后学,广益多闻”,又“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辑出“汇付剞劂”;“有书无可采,而其名未可尽没者,只须注出简明略节,以佐流传考订之用”;至于“本系现在通行及虽属古书而词义无关典要者”,则“不必再行采录”(《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根据这一标准,纂修官逐一检阅当时所存各册《大典》,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相校核,凡有符合采辑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缮写。所缮底本与原书校对后,再撰提要,一并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分别办理。总计先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书,包括著录和存目在内达三百七十五种,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可谓卷帙繁富,蔚为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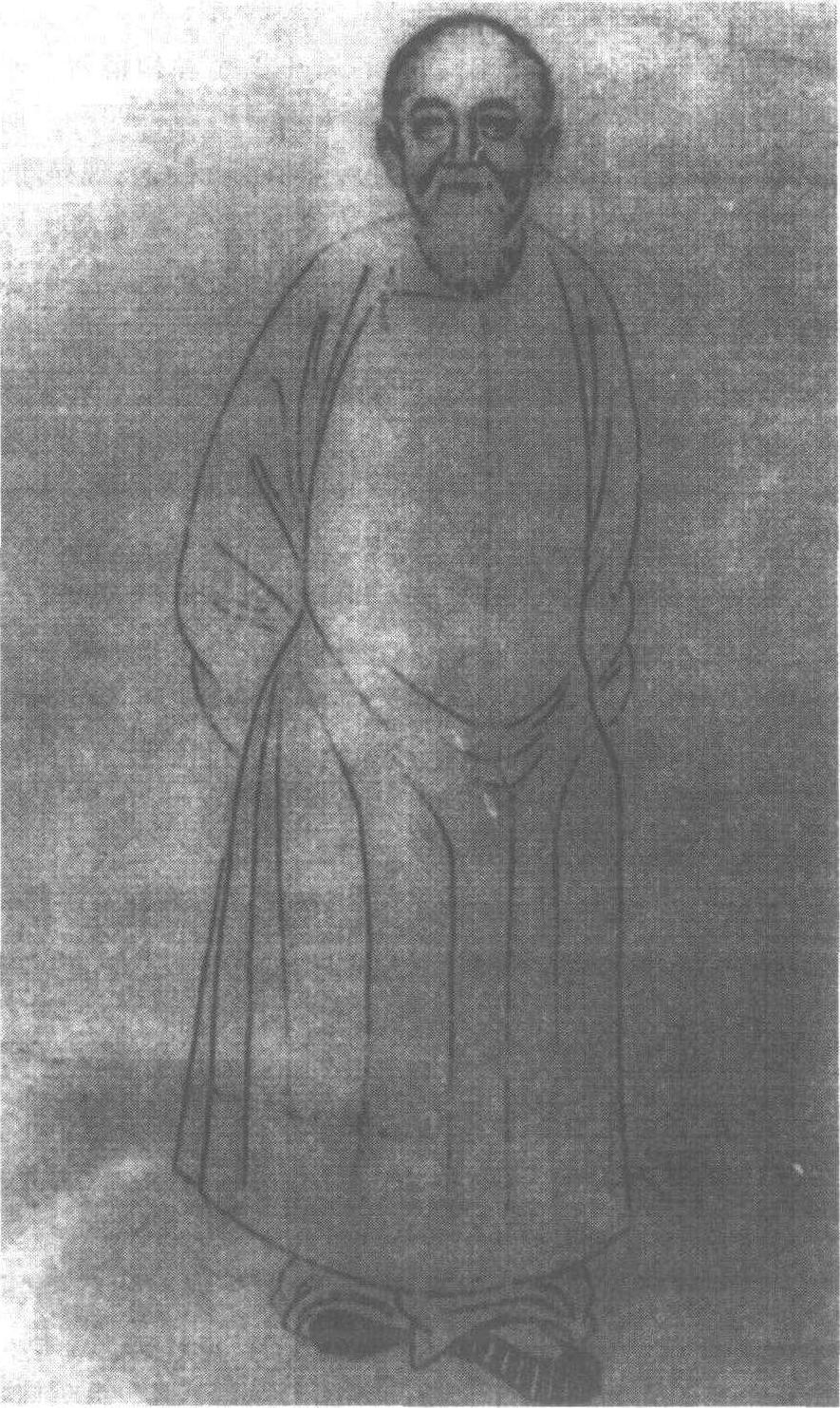
皮锡瑞(1850—1908),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字鹿门,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著有《经学历史》等。
在《永乐大典》辑佚成果的推动下,清代辑佚工作普遍展开。一些学者沿袭四库馆臣的方法,继续在《大典》中搜辑佚书。如嘉庆年间,清政府敕修《全唐文》,参与其事的学者便从《大典》中采辑唐人文集“世所未见之篇”,以补通行本之遗。主持纂修工作的徐松,还利用职任之便,组织有关人员,直接从《大典》中钞出《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等一批卷帙浩博的珍贵史籍。其他学者也相继辑出淳祐《临安志》、《大元海运纪》、《山村词》等佚书多种。在发掘《大典》宝藏的同时,更多的学者则把视野扩展到汉唐注疏、唐宋类书,以及诸史、总集、方志等著述,广泛搜辑周秦古书、汉魏经师遗说、小学训诂之书,乃至历代佚书遗文。风气既开,辑佚在清代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搜采范围日益扩大,方法也日趋精密,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辑佚成果。如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从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藏等各种文献乃至金石文字中搜集唐代以前各家的作品,无论全篇完帙,抑或断章零句,皆汇辑无遗,计收三千四百九十七家,七百四十六卷,被誉为艺林渊海。他如黄奭《汉学堂丛书》,辑录经书八十六种,纬书五十六种,子史各书七十四种,总计收书二百十六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搜辑经书四百四十四种,史书八种,子书一百七十八种,合计收书六百三十种。都代表了清代学者在辑佚方面所取得的可观成绩。
目录清代目录学乃至中国目录学史上的集成之作是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组织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这部大型官修书目的纂修和刊行,对清代目录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乾隆以后,清代目录学出观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各种官撰、私修目录著作数量猛增,并拓展到各个具体学科领域。各类专科目录大量涌现,如经学方面有翁方纲的《通志堂经解目录》、《经义考补正》,史学方面有章学诚的《史籍考》,小学方面有谢启昆的《小学考》,版本方面有黄丕烈的《求古居宋本书目》,金石学方面有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书画方面有官撰的《秘殿珠林(续编)》、《石渠宝笈(续编)》,戏曲方面有黄文阳原撰、董康辑补的《曲海总目提要》,宗教方面有官撰的《大清重刻龙藏汇记》等等。各种特种目录也相继问世,如丛书目录有顾修的《汇刻书目初编》,专人目录有王昶的《郑学书目考》,专书目录有全祖望的《读易别录》,地方目录有邢澍的《关右经籍考》等等。目录著作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促进了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章学诚的《校雠通义》起衰振颓,继往开来,探讨了目录学的性质、作用,目录的分类、体例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继宋代郑樵《校雠略》之后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清代目录学研究方面的显著成绩。
通过上述的择要介绍,可以看到,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长足发展,乃至相对独立成为专门的学科,既反映了清代学者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显示了一代学术所具备的文化价值。郭沫若曾说:“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读随园诗话札记》)可以说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清代学术的长远价值和客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