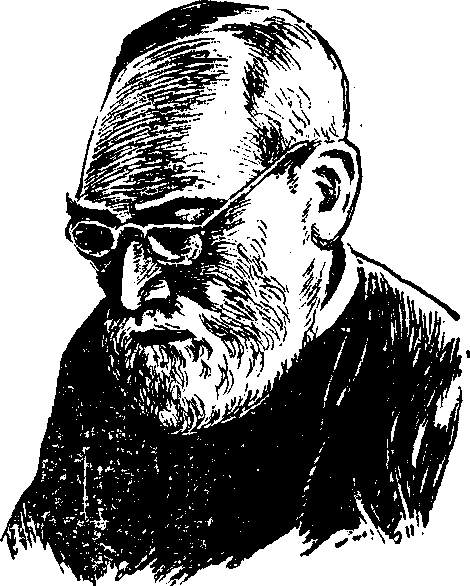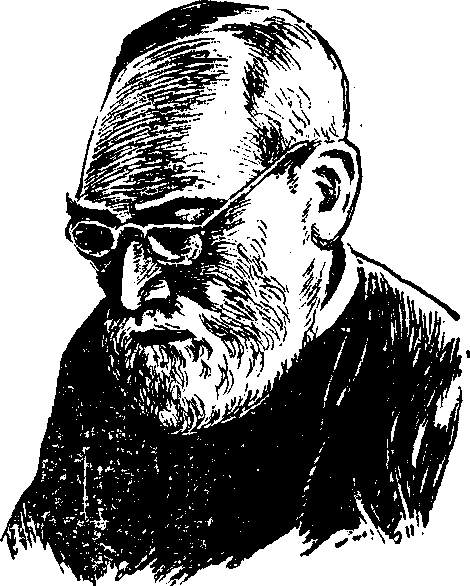
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Surendranath Banerjea,1848—1925),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早期著名的活动家。他的经历之所以特别引人注目,这是由于他早期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非常突出,而在晚年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也比较突出。
班纳吉出生在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里,父亲是著名医生,因受当时孟加拉宗教改革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通。班纳吉在念完大学后,就被送到英国参加文官考试。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1871年被任命为孟加拉西尔赫特县的副治安长官。但他的文官生涯并不顺利,不到一年光景便被除名。他又去英国,希望修完法律课程,将来能进入法律界,但被告知,被除名的文官没有资格当法官或律师。这一连串的挫折对年轻的班纳吉是个巨大打击,但也打开了他的心窍。他由沮丧而逐渐醒悟,认识到他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他是印度人,“是一个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公共舆论,在国家管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民族的一员”。他强烈感到,他的遭遇就是印度“人民极端软弱无力的写照”。
回到加尔各答后,他应邀在民族主义者创办的首府学院任英语教授,后改在自由教会学院教英国文学。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孟加拉正处在建立民族主义政治组织阶段。当时孟加拉主要政治组织是1851年建立的“英印协会”。它是自由派地主的组织,成员限于地主、商人,影响不大。1875年阿南达·摩罕·高士建立了“大学生联合会”,开始在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班纳吉积极参加这项工作。这时他已站到民族主义立场上。他有爱国主义热情,又是个天才的演说家,在各种集会上,深刻揭露印度人民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号召青年们起来争取印度的权利与自由。为了用生动的形象鼓舞青年,他讲述各国人民的斗争史,介绍英雄人物的事迹,最常讲的是意大利民族英雄马志尼。他并不赞成马志尼的革命方法,但认为马志尼的高尚的爱国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印度青年学习的榜样。他要求青年们学习马志尼的精神,用宪政鼓动的方法,争取印度人应有的权利。他的演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这以后,阿南达和他都感到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来代替原来的“英印协会”,这个组织应该主要反映中产阶级的要求,广泛吸收中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参加。1876年,他们共同建立了“印度协会”。
在成立这个新组织的时候,班纳吉希望它成为孟加拉人不分宗教、种姓和社会阶层的大团结的核心。不仅如此,他当时已觉察到实现全印民族主义组织统一的必要性,因而希望把这个组织逐渐变成未来“全印运动的中心”。该组织被命名为“印度协会”用意就在这里。事实上从这时起,班纳吉的视线就不是仅仅集注在孟加拉,而是面向全印了。
为了促进各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全印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团结起来”。英殖民当局的反动政策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877年英国当局决定把文官考试的年龄标准由21岁降低到19岁。这是为了进一步剥夺印度人参加考试从而获得文官资格的可能性。印度民族主义者本来就对英国人垄断印度政府高级职位很不满意,新决定更引起普遍愤慨。班纳吉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一场全印规模的政治鼓动,用反对降低文官考试年龄标准这个共同要求来促进印度运动的统一。
1877、1878年他作为“印度协会”的特使先后访问北印度和西、南印度,进行巡回演讲,征集各界人士在请愿书上签名。他去了许多城市,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新的年龄规定,要求在英国、印度同时举行文官考试,让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在他访问之前,印度许多地区还没有举行过群众性政治集会,所关心的问题还只限于本地区或本教派的个别事情。他的访问像一股强劲的政治旋风,把这些地区都卷到政治斗争的激流中来。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鼓动,其结果不仅表现在形成了一个代表全民意愿的致英国议会的陈请书,更重要的,它开创了在共同的要求下进行全印政治鼓动的先例,促进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随着他的访问,在北印度许多城市建立了印度协会的分支。印度协会成了跨地区的组织。
1878年殖民当局颁布了两项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法令:武器法和印度语种报刊法。武器法规定禁止印度人获得武器;报刊法规定各种使用印度语言出版的报纸必须交纳巨额保证金,以保证不刊载反政府的或带有“教唆”性的材料。这是扼杀民族报刊的反动法律。班纳吉立即领导印度协会开展反对这两项法令的新的政治鼓动,还同来访的“浦那全民大会”的代表一起,召开民族报刊会议,协调应付办法。在共同的斗争中,他进一步看到实现全印民族主义组织联合的必要性。1883年又发生了艾尔伯特法案事件:印度总督会议立法成员艾尔伯特在总督支持下草拟了一项法案,规定欧洲人的案子也可由印度法官审理。这本来是为了用点微小让步平息人民的不满,不料这个法案竟遭到英国人猛烈攻击。结果不但法案受挫,连总督也被迫辞职。印度民族主义者眼睁睁看着发生这种情况,一筹莫展。这件事从反面教育了印度民族主义者,使他们更深切地感到建立全国统一组织的重要性。
班纳吉决心采取坚决步骤来实现这个目标。1883年12月,他以“印度协会”的名义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除孟加拉外,还有北印度许多地区以及孟买、马德拉斯的代表出席。会议通过的决议包括要求让印度人参加国家管理,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立法会议,实行地方自治等。这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召开全印性质会议讨论共同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印度协会”把自己转变为全印组织的最初尝试。
这时,其它地区的民族主义者也在积极筹划建立全印组织。1884年12月,一些民族主义组织活动家在马德拉斯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全印组织。英国退休文官休姆参与了这项活动。休姆担心班纳吉太激进,不让他知道筹划的细节。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当1885年12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成立大会时,“印度协会”等组织召开的第二次印度国民会议也在加尔各答同时开幕。两个会议讨论的内容几乎一样。班纳吉在加尔各答会议结束后立即宣布把自己的会议并入国大党。他这样做是考虑到,第一、国大党包括了全印各地区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更具有全印性质;第二、国大党有休姆参与领导,便于和英国统治当局建立接触,并争取英国舆论支持。班纳吉这个行动是有全局观点的。他虽未直接参加国大党筹建工作,但所有印度民族主义者都公认,他的活动对全印统一组织的建立作了重大贡献。
国大党成立后,班纳吉成了它的最积极的活动家之一。他出席了第二次国大党年会。从那以后,直到1918年他退出国大党为止,这32年中只有一次年会他没有参加。他是国大党讲坛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895年、1902年曾两次被选为国大党年会主席。
在国大党成立以前,班纳吉是很重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但在国大党成立后,不那么重视了。他认为国大党既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由它通过决议或派代表团提出要求,是最好不过的宪政鼓动方式了。所以自从加入国大党,他先前的锋芒也就不见了。
他的观点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没有不同。他也是英国议会民主的积极崇拜者,也同样认为,印度受英国统治对印度未来的发展有无限好处。他称英国为“自由民族之母”,表示相信她会“允许印度这个孩子享有和英国公民同等的权利”。在国大党极端派十九世纪末提出斯瓦拉吉斗争纲领后,他也赞同把自治作为斗争目标,但一再强调这是遥远将来的事,说“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或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争取很快达到自治目的的做法都将危害目的本身”。
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国大党的决议毫不理睬的态度使班纳吉感到愕然和迷惑不解。特别是寇松担任总督后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分割孟加拉,更使他感到惊愕。他认为这是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破坏孟加拉的政治发展。所以,当孟加拉人民起来进行反分割斗争时,他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讲,带领群众宣誓抵制英货。1906年4月在巴瑞塞尔举行孟加拉省会议时,他带领会议代表游行,为此还挨了警察的棒击,遭到拘留。这些行动又恢复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然而,当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时,他就感到格格不入了。
自从反分割运动掀起后,孟加拉极端派就在比·巴尔、奥若宾多·高士领导下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在1905年国大党年会期间,极端派举行了自己的会议,决定把孟加拉的运动转变成为全国运动,把抵制英货转变成为普遍抵制即消极抵抗,以促使英殖民政权垮台。孟加拉极端派从1906年起积极贯彻这个方针。班纳吉面对这种形势感到不安。他参加反分割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分割,并不曾想超越这个范围。所以他竭力劝说群众不要听信极端派的宣传,不要把运动变成反英运动。然而,当他以这种角色出面时,再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演说了。此后,他公开要求停止运动,并于1907年3月亲率温和派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制止孟加拉的风暴,并在总督面前指责极端派“行为过激”。这年年底,温和派在国大党苏拉特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极端派从国大党排除出去,他是积极参与筹划者之一。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班纳吉和其他国大党领袖们一样支持英国作战,希望借此感动英国,换取在印度建立责任政府的让步。然而,战争结束后,英国统治者并不打算马上允许印度自治。1918年公布的蒙塔古—切尔姆斯福德改革方案①表明,英国统治者又把印度的自治推向未来,只愿实行局部改革。在如何对待这个改革方案上,国大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国大党在1916年两派重新统一后,实际上是由蒂拉克掌握领导权。此时蒂拉克的立场已经和温和派相互接近,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蒂拉克和国大党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革方案是令人失望的,他提出了“响应性合作”即有条件合作的主张。班纳吉和原来温和派中的极少数人如瓦恰、夏斯特里等则完全接受这个方案,主张积极合作促使它的实现。班纳吉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英国政府真诚希望给予印度自治,“是向着建立责任政府目标前进的确定步骤”。他认为蒂拉克等国大党领导人的主张是破坏这个美好的进程,有碍国家前途。当国大党决定于1918年8月在孟买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这个方案的正式态度时,班纳吉和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少数人决定不参加会议,并于1918年11月在孟买另外召开会议,成立了一个新党——“印度国民自由联盟”。这样,班纳吉就正式退出了他一生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大党。
当班纳吉的党根据改革法宣布参加1920年的选举时,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开始了。班纳吉对不合作运动发动了尖刻的攻击,说在“政府正准备沿进步路线前进”的时候,掀起不合作运动这种“憎恨运动”是极不合时宜的,并攻击甘地在“玩火”,最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国大党抵制选举,班纳吉的一批人便当选了。1923年,他被任命为孟加拉省地方自治部长。从此,他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地方自治上,而他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在他管辖的有限范围内搞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了。
在回答民族主义者对他改变立场的指责时,班纳吉说:“并不是我们改变了立场,而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和期望有了根本改变。我们欢迎这种改变,并相应地改变了我们对政府的态度。我们要与政府合作来实行自治。在应当合作的时候起来反对绝不是爱国主义,而是背叛自己的祖国。”这不过是用以攻为守的办法来自我解嘲罢了。
不过应当指出,班纳吉的立场确实还是他过去的立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固守宪政改革的传统斗争方式,不肯前进一步。在官场的活动是他在会场活动的继续,参加政府是他参加立法会议的继续。说他背叛祖国,成了殖民主义的鹰犬,是不正确的。
班纳吉晚年采取这样一种与国大党不同的态度,可以这样解释: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在大战中得到发展,战后,资产阶级大多数人主张利用人民的斗争,采取较有力的措施,打破殖民统治的镣铐。但是和殖民统治联系比较紧密的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地主中有些人满足现状,不愿冒险。班纳吉就是后一种人的政治代表。
班纳吉晚年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但综观其一生,正如孟加拉极端派领导人比·巴尔在评价他的作用时说的:无论他一生的经历多么曲折,“他毕生活动的最突出事实”是“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他是“现代印度的复兴者之一”。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